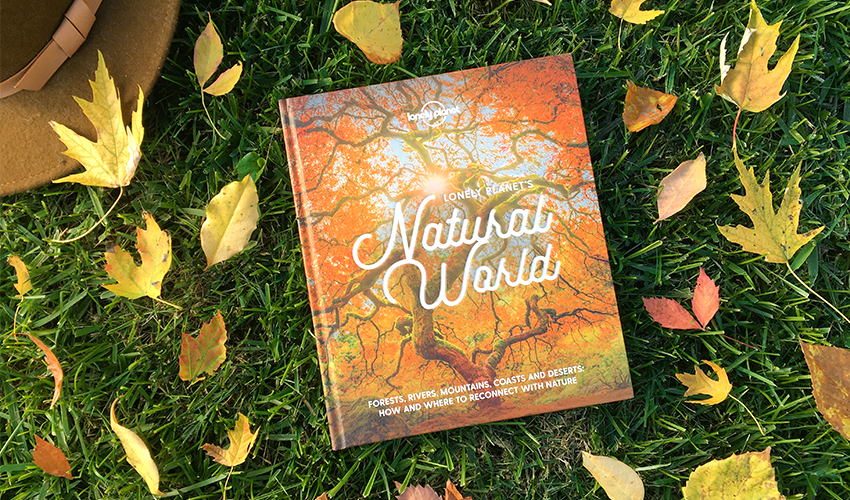在内罗毕,旅行仍然是白日梦

肯尼亚作家凯里·巴拉卡准备开始他的第一次冒险,他希望这将是几十年的流浪。然后,大流行爆发了,并暴露出作为一个非洲人在非洲旅行的挑战。
我想知道,在这个几乎无法旅行的时期,我们丢失了什么版本的自己。我的人生抱负是不再住在任何地方:不再付房租,不再拥有家具,不再支付水电费;把正常的居住维护工作从我的日常生活中移走。相反,我将成为一个巡回旅行者,不断地在路上,在不同国家的不安全的酒店过夜,成为Couchsurfing应用的超级用户,学习如何用多种语言说“你好”和“你昨晚看比赛了吗”。
作为一个孩子,我想成为电视节目的参赛者令人惊叹的比赛,徒步穿过一条小径巴西或者跑到小巷里西班牙,全部搜索线索。在大学,朋友和我教导自己如何说“我不能说这种语言,但我可以在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中讲英语”,以防万一。这是我告诉自己的生命,我会在大学开始生活。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幽灵版本中,我想象我会更快乐。
我于2019年毕业,但越来越跳到旅行的生活中,我经历了长时间的情感危机。在我个人生活中被一系列小悲剧所带来 - 每个人都有几乎无害,但在他们的总和中可怕 - 我逃离内罗毕当时我搬到美国西部的祖父母家上大学肯尼亚.在那里,我的手机大多关机或无法使用,我抽出了自己。我吃了。我读。我写的。我又读了一些。我看了很多浪漫喜剧。我听了很多菲尔·柯林斯的歌。我试图重新平衡自己。

旅行想象
在这期间,我和我的朋友史黛西聊天,她是少数几个我还在联系的朋友之一。史黛西和我从小就认识,但直到最近几年,我们才发现彼此都喜欢旅行,都渴望过一种漂泊的生活。我们交换梦想,直到它们成为旅行路线。最后,我们决定进行一次多国公路旅行,从肯尼亚,到坦桑尼亚,到城市基戈马在坦噶尼喀湖,在赞比亚来维多利亚瀑布.
通过几次电话,我们讨论了日期,制定了预算,并规划了路线。我们开始省钱,我更新了我的护照。我们决定2020年4月是我们的旅行月。
在那几个月里,我感觉到了计划一次旅行的冲动。我们从肯尼亚越过边境,在那里停留阿鲁沙它是坦桑尼亚北部的一个小镇,被认为是世界野生动物之都,因为它与乞力马扎罗太。、梅鲁山和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我们不知道要在那里待多久。自发性是他们的信条。
从阿鲁沙开始,基戈马在西面一千公里处。它位于坦噶尼喀湖畔,靠近坦桑尼亚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布隆迪.我们的计划是花七天时间到达那里,同时在沿途的小城镇停留。也许我们会在恩布鲁停一下。也许Shinyanga。也许Tabora.也许是另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小镇。我们的目标是做一个漂流者,当我们穿过这个地区时发现我们自己。只要我们不破产,我们花多长时间去基戈马并不重要。
我们去基戈马是因为我在书上读到过一艘船,尽管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但它仍然每周往返于坦噶尼喀湖,带着游客去赞比亚。在三天的时间里,这艘红壳船漂浮在世界上第二深的淡水湖上。我对这次旅行和它的历史同样感兴趣。
我知道基础:船只MV Liemba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海军舰队的一部分,在1915年2月5日首次漂浮,但在德国撤退的德国撤退中,它被淹没了,和returned to service by the British in 1927. We’d take that very same ship across Lake Tanganyika to its southern tip, disembarking inMpulungu、赞比亚。这是我第一次在船上。我很兴奋,对晕船很好奇,而且对海水的深度已经很紧张了。
我们估计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穿过这个国家到达津巴布韦的边境。一路上,就像我们在坦桑尼亚所做的那样,我们会发现无名无名的城镇的乐趣。然后我们来到维多利亚瀑布:“Mosi-oa-Tunya”,或者“雷鸣般的烟雾”。我们想象着让浪花洒满我们的脸,沐浴在水的光辉中。
我们还想象着旅行两周后我们会破产,所以瀑布将是我们的最后一站。我们没有穿越边境进入津巴布韦,而是不得不回到坦桑尼亚,我们将使用旧坦赞铁路——这条铁路由中国出资,全长1860公里,于1975年完工,是非洲最长的铁路——然后前往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我们会在达尔呆上几天,躺在海滩上,把最后的钱花在买冷饮上,跟当地人说肯尼亚斯瓦希里语,然后再回去肯尼亚.

旅行推迟
我数着离四月还有几天。这是我恢复时所需要的:第一次多国我们中的任何一个旅行。但是,当然,我们从未离开过家。相反,流行于全球席卷。3月,肯尼亚宣布第一次案件,边界已关闭。政府宣布了一堆限制和宵禁,仍然是一年多的时间。在这里,我们仍然是这次,后来,被困。
疫情爆发几个月后,我和史黛西一起旅行的梦想开始消逝,我在内罗毕的一个埃塞俄比亚餐厅遇到了一位摄影师朋友。天快黑了,再过几分钟就宵禁了,蚊子开始在晚上嗡嗡叫。我们在谈论旅行,我告诉他我去过肯尼亚北部的图尔卡纳湖,也被称为翡翠海。图尔卡纳,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湖泊,穿过边境与埃塞俄比亚.我描述了水是多么的美丽,它如何教会了我玉的颜色的真正含义。
他告诉我他和朋友们的一次公路旅行。他们正经过这里莫桑比克在去南非当一切都出了问题。他们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听到陌生的语言,对自己的安全感到紧张,等待一辆可能永远不会来的公共汽车。我被迷住了,紧紧抓住故事中的每一个新的转折。我很快意识到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我的这种感觉,那就是嫉妒。
对于我们这些未来的旅行者来说,嫉妒并不是一种不寻常的感觉。有时,我们羡慕的是金钱,能够坐飞机去世界的另一个地方,而不必省吃俭用数月。有时,我们羡慕的是护照,并惊叹于签证身份带来的真正自发性。
一场疫苗之遥的旅行
旅行一直不平等。在大流行之前,我们可以依靠,除其他外,签证政治和种族主义持有某些霸权。然而,现在,在这种长期静止之后,Covid-19促使关于这些不等式的新问题以及负责任的旅行看起来像什么。
这种不平等的表现之一是,几个西方国家的人在整个疫情过程中一直在全球南方度假,而反过来则要困难得多。逃离在他们的祖国德国禁止聚会的禁令飞地的dj每周都在坦桑尼亚主要的沿海旅游景点举办派对,特别是桑给巴尔受欢迎的这是西方游客逃离本国对新冠疫情限制的目的地。再往北,是肯尼亚的一个岛屿城镇拉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转变为诺丁山由于富裕的英国人寻求在非洲重新发现自己。在这里,您可以成为一篇文章,“无掩模的袒胸过你最好的生活。
几家西方国家有关于Covid Passports的谈话。逻辑是声音的:毕竟,一个人需要某些疫苗来旅行到一些国家。然而,Covid疫苗在全球南部几乎没有可用。例如,美国接种了疫苗一半只有2.4%的非洲人接种了疫苗。如果旅行必须持有新冠肺炎护照,那么行动就变成了一个双层系统,全球北部在顶层,而我们其他人不幸处于底层。
在Twitter上,我一直在夏天的前景看到人们欢乐,他们所有的派对都会弥补过去一年。欧元刚刚完成,常备者中有成千上万的支持者,疫苗计划的受益者。这一切都不是我的现实。相反,我花了比以前更强烈的孤立所花费的。几天前,Stacy宣传了我们一直在计划的新旅行,这次肯尼亚之旅。我告诉她,我生病了,无法旅行。我没有告诉她它是covid。
你也可以喜欢: